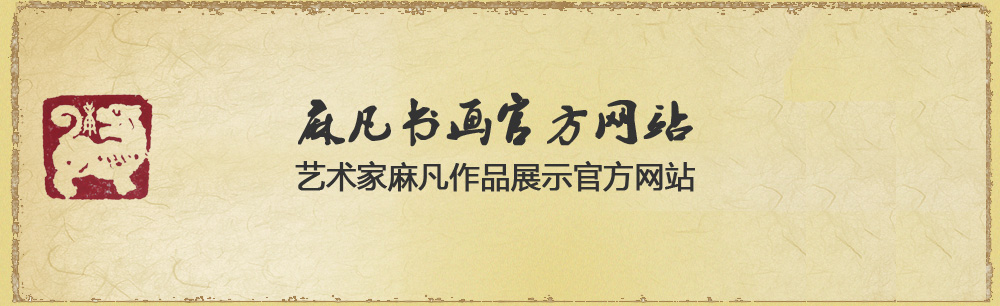七、天人合一话灵璧
在我的藏石中,灵璧石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不仅因为我的家乡离产石之地灵璧县不远,有近石之乡先得石的便利,更源于我与灵璧石的心意相通。
我很少淘石,书斋中的那些灵璧石绝大多数都是朋友所送。有的朋友淘到佳石,来到我处以求点评,说到此石的精妙之处,宾主皆冁然而笑。有时,朋友见我把玩再三,爱不释手,往往慨然相赠,我也就欣然笑纳,或也挥笔写字以回赠。
一次,有位朋友得到一块灵璧石,形丑体瘦,泥屑未尽,反复观看,不解其妙处,知道我喜爱石头,便径直送至我处。我将这块灵璧石掏洗一番,就摆在案头细细观赏。只见这块灵璧石似倒非倒,似斜非斜,恣意伸展,醉态可掬,与“东坡醉石”可有一比。一时兴起,也给此石起名醉石,并赋得新词一阕,《踏莎行·醉石》:“斜枕残梦,醉卧危岫,几杯清酌释宿愁。花落却知西风凉,一盘残局送离舟。陈抟酣睡,刘伶病酒,痴心空惹腊石皱。醉眼醒看须自省,迷离问月缘何瘦”。
灵璧石最大的特点是“天性”、“天色”、“天音”。
“天性”以“张扬”为特点,无规则的外形,无拘无束的伸展,使人体味到一种原始的率真和任性的癫狂。“张扬”的灵璧石没有任何掩饰与装腔作势,只有一种天生的磊落和坦然。
“天色”以“黑”为正宗。尽管灵璧石的色彩丰富,但“黝黑如漆”无疑是它的代表色。灵璧石的“黑”呈现着庄重、沉稳、厚实,它“黑”而不“暗”,“寒”而不“悚”,始终洋溢着一身傲然正气。一石在手,可以很自然地消减当世的浮躁习气。
“天音”以“磬石”为溯源。远在三千年前的殷代,灵璧磬石就被制作成编磬、垂磬、特磬和鱼磬等。灵璧石磬,形、质、色俱佳,扣之有声,克谐八音。
灵璧石被国人爱之、赏之、藏之、颂之,被尊之为“天下第一石”,与灵璧石“天性”、“天色”、“天音”的特点密不可分。因为有了这些特点,灵璧石便呈现出一种朴素、豁达、飘逸的观感,这是大自然的本来面貌。作为赏石者,与灵璧石长相厮守,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解读大自然的密码,久而久之就与大自然相谐相容,不分彼此,回复自然本性、游心天地之间,也就是“石我相融”、“天人合一”的艺术最高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概念,源出于战国子思、孟子学派。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下》)。“诚”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汉代董仲舒说:“事应顺于名,名应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宋代程颐说:“仁者以天下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认为天与人不是合二为一,本来就是“一”。朱熹则更明确地表述为“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朱子语类》)。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合一的各种学说,都在追索天人相通之处,以证天人之协调、和谐与一致。而灵璧石与人的“相融”正体现了这种天人协调、和谐、一致的美。
在中国美学传统中,“一”指的是合乎“自然之理”的“一”,这里不仅表现为一种统一与和谐,而且还能使人感到它在人类发现与创造过程中所显示的“神奇”。美即存在于这种既“神奇”又和谐的发现与创造之中。合于这个要求,一种新质的“自然”才能生成,人所发现、创造的自然才具有合乎“一”的美质。
在大自然面前,人既被制约又是制约者。人在接触大自然时观赏到它的美,这就是自然的“天”,在美的发现创造过程中,人通过自身意志或愿望的手重新创造人所理想的“天”。这个过程就是在原有物质材料的基础上填充自己的内容,使自然具有人自身的品位,成为人的自然。所谓“天”既是自然的“天”,又是被创造的“天”;所谓“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创造着的人。“天”既带着自然色彩,也带有人的色彩。人类不仅从自然中发现了人,体现着人对自然的“精神改造”,自然也对人进行人性、人情的渗透。灵璧石与人的关系,正是这种过程的完美体现。
观赏灵璧石的过程,就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展示过程。作为一名赏石者,不仅要有灵璧石之眼,更要有灵璧石之心。由此,方能通过观石观已以类情德。灵璧石生命的节奏和性情反映的是一种内涵无限深奥的象外之意、景外之情,给赏石者的心灵一种致远感悟。将自己投入灵璧石中,还人之天性、达到“天人合一”、“石我为一”的艺术之最高境界。
古往今来的赏石者中,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不乏其人。
南唐后主李煜收藏有“灵璧研山”,据《铁围山丛谈》记载:此石径长愈尺,前耸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高者名华峰。参差错落者为方坛,依次日岩、玉笋等。各峰均有其名,又有下洞三折而通上洞。左右则因两岸陂陀而中凿为砚。李煜十分珍爱,在兵临城下,江山易手之时,仍痴迷“国破石头在”,宁愿当俘虏也舍不得丢下石头逃命,最终被俘,真可谓不恋江山爱美石。
米芾与灵璧石有着不解之缘,趣闻轶事颇多。《古今谈概·癖嗜部》中记载:米芾守涟水,地近灵璧,蓄石甚富,逐个品第,加以美名,入室把玩,整日不出。杨次公杰为察使,因往涟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整天弄石,不省禄郡事?”米芾于袖中取一石,嵌空小巧,峰峦窟窿皆具,色极青润,婉转重复,以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袖。又出一石,叠峰层峦,奇巧更胜,又纳之袖。最终出一石,尽天划神镂之巧。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惊见之下,遽然趋前曰:“此石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撄得之,登车迳去。米以杨夺其所最,惘然自失累月,屡以书请之,竟不复得。
米芾爱石、拜石、痴石,在常人眼里好像违世异俗,孰不知米芾在书法、绘画上的深邃造就,正因为他体石悟道,丘壑内营,活化了他的精元灵愫,才创造出跌宕跳跃、飘逸超迈、天真自然的书法艺术。
叶梦得宠爱灵璧石“良是一癖”。在他所著的《石林记》里这样写道:“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见于诗味者,来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所谓“自不能解”,即人石之机缘。灵璧石外在奇特表现和梦幻般的神韵与癖石者的情感相冥合,致使“心犹爱之不已”。有一次,叶梦得病中得到一块灵璧石,竞然抱之睡觉,高兴得连病也好了。叶梦得痴迷到石人合一、人石相融、视石非石、如梦如幻的境界,正是灵壁石无穷魅力之所在。
蒲松龄也是一位超级石迷,《聊斋志异》中的《石清虚》一文,就是他爱石如命的自我写照。故事叙述邢云飞好石,见佳石不惜重金求购,配以檀跌,供诸书案,以命相许,共存共亡。蒲松龄笔下对人石感应,天人合一,缘缘相报的刻划,达到了神化、仙化的艺术境界,是一曲绝妙的石文化乐章。蒲松龄将他最心爱的十块灵璧石称为“十友”,依石之形象赋以“凤翔”、“双鹰”、“九象”、“峨豸”、“太朴”、“垂云”、“菡萏”、“月窟”等名,并题《十友》诗:石隐园中远心亭,门对青山四五层。凤翔双鹰飞禽样,九象峨豸走兽形。太朴垂云生得好,菡萏月窟最玲珑。宁朝魁星石灵璧,万世流传十友名。
一石尽揽世间趣,一块块灵动雅逸的灵璧石在记述着它的不凡。当然也有些灵璧石本身就已经非常完美,并不需要我们再去发现或者做什么修饰打扮来画蛇添足,只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慢慢品读感悟灵璧石本身的美和哲理。当我们的身心因此获得愉悦或是顿悟时,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