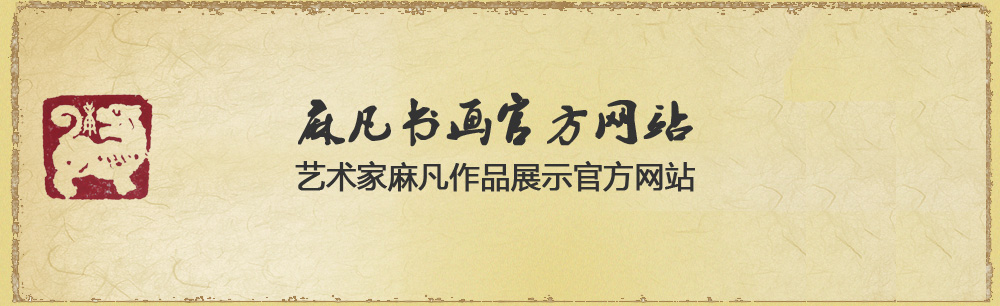麻凡文集‖第九辑:读经偶得(上)‖ 七、游于艺
七、游于艺
艺术界有一句名言:游于艺。这句话年头久了,是二千多年前孔子说的,出自《论语·述而》第六章,原句如下:“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为:“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用大白话讲:没有高远思想就未免太俗气;没有德行为根据,人生就没有根基;没有仁的内在修养,心灵就没有安顿的地方;知识学问不渊博,人生就枯燥了。
孔子的这句话这实际上是他培养学生的教学方案,他是以道、德、仁为纲领,以六艺为基本,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孔子对“道、德、仁、艺”四点都很重视,现代人对这四点各有偏重,艺术界基本上就剩了“游于艺”。
对“游于艺”的解释古今各不相同,这大概就是时代性所致。我们先来看一下古人是如何“游于艺”的?
首先何谓“游于艺”?“游”的古字形有:斿,遊,游三种,甲骨文中无从水之“游”,只有“斿”,写作:,由(旗)和(子)组成,飘扬的旗帜下面有学子。篆文加了“水”(河)另造“游”代替,表示古代学子打着族旗,过河越境,四处参观学习。当“游”引申出“泅水”的稳定义项后,后人以“辵”代“水”另造“遊”,表示陆上的巡行。《说文解字》注:“遊,旌旗之旒也。”由于旌旗所垂之旒,随风飘荡而无所束缚,故而与“遊”通,且引申出来的涵义与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联系。因此“游”从根上带有逃脱束缚、自由自在之意。再看“艺”字,甲骨文写作,由(生,表示幼苖生长)和(执,一个人张开双手在劳作)组成。“艺”是禾苗的嫩芽,是人的创造物,《毛传》云:“艺,种也,种之然后得麻。”《尚书金滕》“乃元孙不若旦多才多艺,不能事鬼神。”因而,艺引申为才艺、技艺。从字面上看“游于艺”即是对六艺的掌握,并从中体会到自由的心境和精神的愉悦。
古人有很多“游于艺”的故事。《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了一件非常有名的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个故事讲的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字子猷)退隐会稽山阴时的事,那天夜里下着大雪,王徽之一觉醒来,已是子夜时分。他便命仆人打开窗户,拿些酒来,一边喝酒,一边眺望远处。只见白茫茫一片,王徽之心中有些彷徨,于是口中念起了左思的《招隐诗》,念着念着,忽然又想起了剡溪的好朋友,当时的一代名贤戴逵(字安道),并决定去拜望他。山阴与剡溪相隔百余里,王徽之乘着酒兴,不顾天寒和路途遥远,连夜乘船溯江而上,船行百余里,到第二天中午才来到戴逵的家门口,他正准备敲戴逵家的门时,突然停住了。此时的王徽之不但没进门去拜访戴逵,反而吩咐仆人掉转船头回家。有人问王徽之,你不辞辛苦远道拜访朋友,为什么到了朋友家的门前,又不进而返呢?王徽之坦然回答道:“我本是乘酒兴正浓之时而来,现在酒兴已消失殆尽了,那么见到戴逵又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王徽之雪夜访戴逵的佳话,也是“游于艺”自由心态的绝佳表现。
“游于艺”到了极致,便会如庄子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睥睨于万物”。米芾素以癫狂任性著称,他爱石,便拜奇石为石兄,他爱砚台,为了一方砚,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顾大雅。一次宋徽宗让米芾以两韵诗草书御屏,实际上也想见识一下米芾的书法,因为宋徽宗也是一个大书法家。米芾笔走龙蛇,从上而下其直如线,宋徽宗看后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大加赞赏。米芾看到皇上高兴,随即将皇上心爱的端砚装入怀中,墨汁四处飞溅,并告皇帝:此砚臣已用过,皇上不能再用,请您就赐予我吧。皇帝看他如此喜爱此砚,又爱惜其书法,不觉大笑,将砚赐之。米芾捧着端砚,高兴万分,手舞足蹈,“余墨沾渍袍袖”也在所不惜。宋徽宗见状,对蔡京说:“癫名不虚传也。”米芾的“癫态”实际上是“游于艺”到了极致的所致。
到了二千多年后的现代,“游于艺”的概念仍然贴着孔圣人的标签在使用,但实际内容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就说“艺”,古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基本上可以涵盖所有“艺”的门类了,现代人被要求的技能就多了,如考研的英语、政治;应聘的各类证书、学历、驾驶技术等等。现在的“艺”有多少门类,可能谁也数不清。
再说“游”,在孔子时代,“游”应是熟练掌握各类技能,即六艺,如鱼之在水,从而获得自由和愉快。现代的“游“,一般是指与你所专的“艺”有关的一切技法都要熟练掌握,在此基础上,摆脱各种杂念和有限世界,进入高度自由、向无限世界腾跃的状态,也就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与灵性的自由流淌。“游”这个关键字不仅显露出艺术家的生活倾向和艺术态度,还蕴含着艺术的诗性品质与纯粹的审美乐趣。这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它超越了生理感觉和物质功利进入更高的心理层面,在这种状态下创作的作品,可称为“神品”、“逸品”。从一些大师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以轻松的心态,自由的精神进行创作,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作品中许多神来之笔完全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作为一名书法工作者,我对“游于艺”有着自己的感悟。每天上午是我的创作时间,此时,我杜绝一切应酬和杂务,让自己进入一种澄明空灵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拿起笔,自由挥洒生命中不可抑制的律动与激情,忘情地书写我自拟的或借用的文字,在运笔施墨过程中感受得意忘形的快感。此时的我对于所习之“艺”来说,犹如鱼在水而忘其为水,斯有游泳之乐也。我的这种创作状态是摆脱一切世俗的、功利的、器物的羁绊,完全回到人的本性,使心灵有着更为开放,更为广阔,更为纯净,更为适合想象之自由,更彰显人格的自我张扬,这就是“游于艺”。
“游于艺”其实是需要条件的,庖丁解牛在于他能够自如地运用手中的解刀,而在此之前,这位庖丁可是练了几千次、几万次运刀技巧,用钝、用毁了多少把解刀,也只有他自己清楚。艺术创作同样如此,我是从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开始,这是前提也是基础。除此之外,宽裕的空间、自由的时间、旷逸的心志、渊博的学养,这些都是“游于艺”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你蜗居在一个斗室里创作,下锅的米还等着微薄的润笔费,这时,哪怕你熟读刘禹锡的《陋室铭》,也不得不向五斗米折腰。在这时候,如果要说“游于艺”的话,只能是一句空话,恐怕要换一个字,就是“囧”于艺了。
本站由华籁网络提供技术支持,未经麻凡书画网授权禁止复制或镜像本站任何数据,否则必究!
CopyRight 2009-2012 mafanshuhu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麻凡书画网 - 艺术家麻凡作品展示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