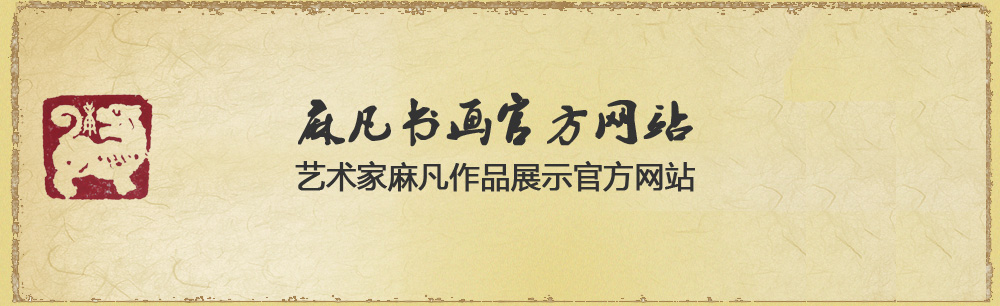四、话说文房四宝——砚
砚,在文房四宝中忝列末位,但是,砚所涵纳的砚文化当属国粹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一族,在华夏的文明史上,砚对传播中华文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要追寻源头,砚的历史极为悠远。汉代刘熙《释名》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研,就是研墨的工具,也称研磨器,它的作用和后来的砚台几乎一致,或者说,研就是原始的砚,是文房四宝之一——砚台的源头。
那么,这个源头最早出现在哪里呢?宋代苏易简在《文房四谱·砚谱·叙事》中说:“昔黄帝得玉一钮,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研’”。这段叙事告诉我们,早在黄帝时代就有用玉琢制而成的研。虽然这只是文字记载,并没有实物佐证,但是,地下文物却将这个佐证完美的呈现出来。在西安仰韶文化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精致的研磨器,其长51厘米、宽26厘米、厚约5厘米,周边打制和打磨痕迹明显。中部略低,有一个横向的椭圆形砚池,旁侧还有一个竖向的椭圆形砚池,并附着有少量的红色颜料。
如果说,仰韶文化遗址的研磨器只是单一的佐证,还不能有充分的说服力,那么,我们再看1979年在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研磨器。这件研磨器的器面上有凹处,用以集聚颜料汁水,凹处还搁置着磨棒和天然颜料,旁边还有一块盖板。这个研磨器除了比较简陋粗糙之外,本质上与现代的砚台已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有需要就会有市场。在仰韶文化期间,先民们已经开始在陶坯上描绘黑色、红色的花纹、图案,这就需要调制好的颜料,用来研磨有色矿物颗粒的研磨器也就应运而生。随着文字的产生,文字所需要的书写工具,如墨、笔也开始出现,专门用来研墨的研磨器从研磨器的大家族中分离而出,自成一体,到春秋时期由研磨器发展而来的砚台基本成型。由于早期的墨为颗粒状或薄片状,未能作成墨锭,不便握持,故秦、汉古砚多附有研子(研杵、研石),用它压住墨粒研磨。
秦汉时期的砚与汉代以后各朝代的砚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秦汉砚在研墨时仍需要研石或杵棒相助,另一方面,由于当时适合书写的纸还没发明,人们对墨的质量提不出高要求,更谈不上对砚石的研墨能力即发墨效果的注重和选择。应该说,秦汉砚只是初步摆脱了原始砚“只求实用,不求美观”的风格,但由于历史条件及需要的限制,还处在极不完善的初创阶段。
汉代以后,中国的砚台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完善。东汉末期,蔡伦发明的纸已完全普及开来,制墨技术也已成熟,研墨不再需要研石相助,人们对砚台有了更高的要求,如发墨、细腻、滋润等等。砚台的砚质、砚形由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这是当时人们追求和评价良砚的表现。
汉代以后,古砚由简单的研磨墨粒、墨片,演化成材质众多、形制各异的庞大家族,并集雕塑、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及众多藏家追捧的珍贵藏品。
说起砚的收藏,一般人都把中国的“四大名砚”作为收藏的重点对象。这四大名砚分别是:唐代时出产于广东肇庆的端砚,晚唐时出产自安徽婺源的歙砚,东晋时产自山西绛州的澄泥砚,宋代时出产于甘肃临潭的洮河砚。
在古砚的收藏中,砚文化始终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砚台本身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历史变迁,从独特的角度诉说着朝代的更替,而砚文化也就成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个独特部分。可以说,每一方名砚背后都凝结了浓厚的文化内涵,凝聚了中国人的记忆和历史的气息。
特别是铭文砚,自唐以后历史上的各朝文人墨客、官僚富商都喜好藏砚,对自己使用过的古砚,往往都留下铭文题识,这是砚台中最受人青睐的一种。砚台上的铭文可能是一个人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座右铭,也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悟出的至理名言。铭文砚可以讲述一段历史,可以印证一种精神,还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因此,在收藏中凡是和历史名人、历史事件有关的铭文砚价值相对更高。
被人津津乐道的玉带生砚就是这样一种铭文砚。玉带生砚属稀有珍贵的端溪老坑石材,砚身有一石脉,若隐若现,浑然天成,砚形制古拙浑朴,透发出沧桑气息。此砚是我国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遗物,砚盖上镌有文天祥手书砚铭:“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潾潾,中之藏兮渊渊,外之泽兮曰宣,呜呼!磨尔心之坚兮,寿吾文之传兮。”字体遒劲秀润,气韵生动,显示出砚主人是位颇具造诣的书法家。据说,玉带生砚是南宋爱国诗人刘辰翁所赠,他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等都是朋友,志同道合,但他对文天祥寄予的希望最大。文天祥一直将玉带生砚带在身边。他的《正气歌》、《金陵驿》等不朽的传世名篇,也正是蘸此砚所研之墨写就。文天祥就义之后,这一珍贵遗物遗落世间。清代中叶,文天祥的玉带生砚几经辗转,流入清宫,成为乾隆皇帝御用之砚,视若拱璧,亦不常用,置藏于三希堂内。乾隆雅好诗文,特意在这方玉带生砚上镌下他创作的《玉带生歌》,共169字,这首诗赞美了此砚的不同寻常,且借此褒赞忠于南宋、舍生取义的文天祥。清末,这方玉带生砚从清宫流失出去,不知所终,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玉带生砚的砚铭拓本,为明末清初知名文人朱彝尊所拓。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民间的文氏宗亲会将这方玉带生砚寄到文天祥的故里江西省吉安县,被该县文管部门收藏。这方玉带生砚如何到了台湾,这段经过已难查考。
还有两方铭文砚谱就了一段传奇。明末清初才艺品貌双绝的艺伎柳如是仰慕侍读学士钱谦益博学多才,发誓“非才学如钱学士者不嫁”。时年59岁的钱谦益冲破世俗的阻力,将24岁的柳如是迎娶回府,专为小妻盖一楼,名为如是楼。夫妻二人各置一砚,铭款题词,日常书字作画,各用其一。二人去世后,其砚散落民间不知所终。
1945年冬天,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应邀去名士溥雪斋家中赏砚,想不到那砚竟是有铭款的“如是砚”。先生大喜,死死抱住那砚不肯放手,一定要溥先生割爱。溥雪斋见张伯驹爱砚如此,也只好成人之美。
张伯驹当晚挑灯赏砚直到夜半。翌日清晨,有人敲门,是琉璃厂一古玩商人,说是前些日子得到一方古砚,特来请先生“鉴赏”。商人解开布包,先生大吃一惊,竟是“谦益砚”!
这两方夫妻砚阔别200余年,竟然鬼使神差似地于朝夕间相会于张宅。名砚因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天然材质和精湛的工艺技术,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喜爱的藏品。宋代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砚谱》中就明确指出:“端州圆石青紫色者,琢而为砚,可值千金。”到了现代,名砚仍然价值高昂。1992年,香港拍卖市场上出现一方十七世纪出品,被国画大师张大千收藏过的端砚,拍出了38.5万港元的高价。
收藏砚台,需要广闻博见,积累丰富文史知识和考古知识,在鉴赏时,可以从质地、工艺、铭文、品相、装饰等方面分析。
收藏和发现一方好砚台,需要专门的知识进行判断,也需要通过触感来判断。一般来说有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是看其外形。砚台需要经过清洗才能辨认。古砚的砚面上墨痕斑斑,遮掩了石材的天然纹理,也难以断定其年代和品相。看外形,重点在于看砚台的品相、工艺、铭刻、质量、装饰与新旧等。而造型品相则一般以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为上品。
其次是触其石,可以用手触摸古砚体会其质感。如果感觉光滑,说明石质较好,如果触感粗糙,则意味着石质较差。好的石质,可以让砚台充分发挥其辅助书写的作用。所谓“夏天储水不易腐、冬天储水不易冰”,正是好砚的标准。还可用手掂量砚台轻重,如果大小相似,砚石重的结实致密,尤其对于歙砚而言,密度重量是重要考查因素。
最后是听其声,五指空托砚台,轻轻击打砚面。如果是歙砚,清脆的“嘡嘡嘡”金属声者为上品。此外,除了砚台本身作为文化的载体,砚台的文化附加值也被高度重视,包括是否有铭刻、装饰、名家背景等。
通过对中国砚台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砚台从起源到成熟,再到完善,绵延五六千年,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步。如果你想对中华文明有所了解的话,不妨加入中国砚的收藏行列,你会发现其趣融融,其乐无穷。